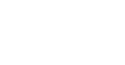你像我,我也像你,但为什么是你被选中呢?
几年前,我碰上一个偶然的机会,算是志愿性质地陪同几个美国家庭游桂林。对于这个商业化十足的旅游胜地而言,这群金发碧眼的老外只是非常普通的游客。唯一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手中所牵着的少女们:清一色的黄肤黑发凤眼和黑色瞳仁,却清一色的地道美式腔调。
路上,无数的行人都纷纷侧目,投出好奇甚至怀疑的眼色,夹杂窃窃私语和放声谈论。而那几个十岁左右的姑娘,她们前前后后雀跃着,叽叽喳喳,就像盛夏时漓江上跳动的阳光。
家长湿润而浓烈的目光像是被钉在了这些女孩的身上,其间他们不止一次蹲下来对自己的中国女儿说:看,这就是你的家乡,很美吧。
从弃婴到小明星
埃德和帕蒂一家是这次“寻根之旅”中的一份子,他们前后收养了江浙的两名弃婴:塞瑞与艾茉莉。
2004年秋季,12岁的塞瑞(Sarah)获得了由总统布什签署的“全美优秀学生奖”,这在几乎所有美国学生眼中,都称得上是最高荣誉。其实早在获奖之前,塞瑞那超于常人的天赋就已经开始显露了。小学时,与其他二十几名白人同学相比,班主任说塞瑞的智力、记忆力和英语水平,皆列全班第一。她喜好文娱,跳舞的大幅剧照不止一次登上了州里的报纸,还是市里的少年体操队队员。
这一定是她的亲生父母所无法想象的吧。 1992年,埃德和帕蒂从江苏省常熟县将4个月大的塞瑞带回了美国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,两年后,他们又飞向中国浙江省建德县,这一次,抱来了3个月大的艾茉莉。
他们并非大富大贵之家,只是最平凡的美国家庭。丈夫埃德是百事可乐公司的一名雇员,工资并不太高;妻子帕蒂曾是公务员,原本在待遇较好的石油部门任职,但后来为了能更好 地教育并陪伴这两个女孩子,她决定辞职,选择到一间离家较近的小学上班,薪水是从前的一半,而且工作也比先前要繁琐得多。自从收养了这对中国姑娘,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算不上宽裕。
即便如此,夫妻俩为了培养这两个中国女儿,从来不遗余力。从1999年开始,她们先后参加了业余体操学校的培训,后来塞瑞还另报了中国舞蹈班、艾茉莉则选了小提琴班。于是埃德和帕蒂每天下班后,就一人带着一个,赶场子似的陪着她们去学习。
平日在家里,这对夫妻也在尽可能地营造某种浓郁的中国气氛。他们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装帧精良的国画,分别是烟雨蒙蒙的江南和乡村牧童吹着笛子自娱自乐。而自从有了这对女儿,他们一家每年所过的节日比普通美国家庭多出了一倍,不管是美国的圣诞节、复活节、感恩节,还是中国的春节、元宵节、中秋节,无一遗漏。
同时为了让塞瑞和艾茉莉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、能更好地学习母语,帕蒂每天下班后都带着她们去CCAI的中文语言班学习,而这对于一个年过40的地道美国中年妇女而言,实在不是什么好玩又省劲的消遣,但帕蒂还是希望孩子能“从接触中国文化而热爱中国”。
令帕蒂欣慰的是,塞瑞喜欢她所学的这一切课程,她经常一个人练习发音,并且用中文去写一些简单的字条给帕蒂,甚至在家里闲着的时候,经常找机会试着使用她的这门“第二语言”。
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”
相比于塞瑞的耀眼夺目,妹妹艾茉莉似乎要更“邻家”一些。但或许是孩子的天性使然,艾茉莉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上,都总是不自觉地爱和姐姐争个长短。
他们俩自幼各居一室,房间里设备一模一样,衣服、玩具、摆设和课外书也都是半斤八两。在这一点上,埃德和帕蒂非常擅于将一碗水端得四平八稳。
尽管如此,艾茉莉有天却还是找到了耍小性子的借口,她忿忿不平地问道为什么她的房间里只有一扇窗户,而姐姐的房间里却有两扇呢?
另外一次姐妹俩在客厅玩多米诺骨牌,玩着玩着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拌起了嘴。帕蒂坐在一旁不开腔,想看看她们自己怎么解决,最后塞瑞与妹妹吵了起来,她才出面干预。谁知当时才10岁的艾茉莉满腹委屈地对妈妈抗议道:“You spoiled her!(都怪你把她惯坏了!) ”
夫妻两人对我们谈起这对姐妹的囧事和趣事,不由得哈哈大笑。但当被问到是否确实对塞瑞略有偏心时,他们却一下严肃起来,帕蒂说:“塞瑞确实优点多一些,也总受到学校表扬,可能这对艾茉莉来说是种压力,她就容易觉得我们对姐姐比较好。但其实在我和埃德眼里,孩子就是孩子,无论优点缺点、聪明不聪明,她们都是一样的, 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。”
尽管埃德和帕蒂对这两个女儿疼爱有加,却从不溺爱。他们没有请过保姆,姐妹俩平时的零花钱必须靠帮助父母做家务才能获得。在这个家里,你会看见房间里的东西被收拾得有条有理,地板也光可鉴人。
平时,艾茉莉经常会主动抢着干活,但每次攒到钱后她都舍不得花,一点点把它们给存进了银行。这么一来,在她还不到10岁时,就已经通过做家务挣得了两千多美元。
埃德说,在理财上,艾茉莉就比姐姐要强得多了。塞瑞总是一赚到钱,随手就用掉了。“可见上天是多么的公平啊,哈哈。”
我的父亲与埃德夫妻是多年的老朋友,2004年他去美国时曾拜访了这一家。短短一星期的相处中,他亲眼所见这对夫妻智慧与恩慈并重的教育方式、他们怎样尽最大努力去调和着两个姑娘心中对于“血统”与“身份”的隐隐矛盾,最重要的是,怎样去爱她们。
临走时,艾茉莉提出要为我父亲拉一首小提琴曲送别,音符才刚飘出来几个,他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那是《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》。
稚嫩的乡愁
随着女儿日渐长大,埃德与帕蒂心里也有自己的苦衷。
“我和埃德是幸福的,但是对于塞瑞和艾茉莉而言,她们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这是一件多么难以弥补并且永远无法消失的痛苦呢。我们每天都在想,想怎么找一个适当的时候、用怎样合理的方法,让她们能接受这种现实……”帕蒂说。
我们站在漓江的渡轮上,我扭过头来看这位四十多岁却已是头发花白的母亲,操劳的痕迹不动声色地写在了她的脸上。
同样的困顿似乎也时不时搅扰着塞瑞。为此,她写了这样一首短诗:
我为什么?
为什么呢?我在担心的颤抖中问道。
今天请你耐心聆听
为什么内心常有争斗
就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?
你像我,我像你,难道你就为此而选中了我?
啊,请停下吧,请停下吧
你我唯一的不同之处,就因我出生在另一块土地上?
我已经想过了,这毕竟是件悲惨的事情
你像我,我也像你,但为什么是我被选中呢?
为老家常熟县福利院写这首诗时,塞瑞刚满12岁,就像她母亲帕蒂所形容的:sensitive(多愁善感)。常人实在难以想象,这个年纪的少女,究竟为什么会对几千公里外的从未踏足过的故乡,有这样复杂而强烈的感情。
我突然想起了仲辉与聂立立的理念:不仅要替这些没有家的孩子找到“家”,并且还要在他们长大成人的漫漫道路上,让他们也找得到“国家”。
于是在塞瑞和艾茉莉都成了挺拔少女之后,埃德夫妇决定带着两个女孩回中国“寻根”,为此,他们从两年前就开始存攒积蓄了。
他们先后到了北京、成都、塞瑞和艾茉莉被收养的两所福利院,沿京杭运河游苏杭,再到广西看了看“山水甲天下”的桂林,最后从香港飞回美国。
我和他们到了桂林才见面,在此之前,我和塞瑞已经断断续续写过好几封信,所以并不算太生疏。一路上她和艾茉莉都试图用蹩脚的中文跟我对话,但有时某个词某句话在嘴巴里转悠半天吐不出来,就又不得不转回英文频道。
她们讲到长城的雄伟、西湖的妩媚,也讲到看见福利院里那一个个孩子时,自己心中涌现的感伤,“多希望她们都能像我和艾茉莉一样找到爸爸妈妈呀”,塞瑞说着说着就在大太阳底下红了眼眶。
尽管中国有再多的好,她们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成长的地方。 “不太吃得惯这里的东西……”艾茉莉每口饭都嚼得索然无味,出来半个月,她实在想念牛排、沙拉和薯条。
“而且我从来没想过中国竟然有这么多的人,虽然看着周围都是跟自己长得差不多的脸,那种感觉挺幸福的,但实在是太挤了……”塞瑞说,而且她也不喜欢四处都是叼着烟的人,一路上她经常被熏得咳嗽。
虽然心底有着不知出处的乡愁,但其实骨子里,她们都已经是彻头彻尾的“American Pie”(美国少女)了。
更多精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