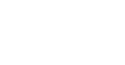《我们生活在巨大差距的世界里》--余华
《我们生活在巨大差距的世界里》
在南非我感受到什么叫广袤的大地,不是一望无际的平坦,而是不断起伏的扩展。葵林、仙人掌、灌木和树木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视野里,有时它们又是孤独地形影相吊。金矿和煤矿相隔不远,焚烧野草的黑烟与火力发电的白烟在远处同时飘升……在变化多端的大地上,我感到最迷人的是向前延伸的道路,神秘又悲壮。
命运的看法总是比我们更准确。
索韦托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标识,超过一百万黑人被驱赶到这里,无电无水拥挤在狭窄屋子里,出门需要通行证和进城证。如今的索韦托有电有水,也有宽敞的道路,可是昔日的苦难还在显现。当年黑人带来很多装满衣物的纸盒堆在家中,很多人没有打开纸盒,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家。这些人直到死去仍然没有回家。
记得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流行一个段子:这个开幕式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为什么?一,有这么多人的国家,没有这么多的钱;二,有这么多钱的国家,没有这么多人;三,既有这么多人又有这么多钱的国家,没有这么多的权。
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,不平衡的生活。区域之间的不平衡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,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,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,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。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,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。即便什么都没有了,只要还有梦想,就能够卷土重来。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。
乌拉圭队在精彩跌宕的比赛里最终点球战胜加纳队。我想起曾经有中国记者问瑞典学院的一位院士:“冰岛不到三十万人口,就有人获得诺贝尔奖;中国有十三亿人口,为何没人获诺奖?”这样的比较很幽默,好比有人问布拉特:“乌拉圭只有三百万人口,可是他们的足球运动为何强于十三亿人口的中国?”
巴西出局,阿根廷球迷幸灾乐祸;阿根廷出局,巴西球迷兴高采烈。看到对手身上的伤口会暂时忘了自己的疼痛。贝利和马拉多纳的对立,就是这两国球迷的对立。这时候很多中国球迷正在为他们的共同出局难过,别人的伤口却是自己在疼痛。究其原因,可能是自己的足球一无所有,现在连伤口和疼痛也没有了。
冯小刚说中国电影像中国足球;以前有人说中国文学像中国足球;股市低迷时有人说中国股市像中国足球……其实中国足球这些年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,拿它作比喻来发泄愤怒和不满很安全,既不会犯政治错误也不会犯经济错误。
十多年前,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,美国诺顿出版公司当时的董事长兰姆先生对我说:“你知道什么是媒体吗?”他坐在家中的沙发里,舒适地伸出食指,向我解释:“比如你的手指被火烧伤,如果媒体报道了,就是真的;如果媒体没有报道,就是假的。”
在美国一年只出版两万多种图书。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美国时,美国每年出版十二万种图书,中国是十万种。此后几年中国出版数量迅速超过美国,今年达到三十万种以上。金融危机后美国自动削减出版数量,现在一年只有两万多种,而中国的出版数量仍然每年递增。中国这种没有节制的发展,让我想起一句什么人说过的话:知道自己无知不是完全的无知,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。
二○○八年春天我在为《兄弟》法文版做宣传时,遇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女记者,四十多岁,性格开朗,不断张嘴大笑。采访结束后,她告诉我,她小时候有很多中国人到多哥帮助种植稻米,这些远离家乡的中国男人大规模种植稻米的时候,也大规模和多哥女人做爱,留下了大规模的混血儿。这位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一个中国农业技术人员留下的孩子。说到最后,这位多哥裔的女记者放声大笑,她说多哥曾经流行过一句谚语:“中国人留下的孩子比留下的稻米还多。”
阿斯比旺大把抓着肉片鱼片吃,大口喝着从赤道回来的烧酒,大声讲述起他二十岁时曾经吃素的故事。那时候他住在巴黎,有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朋友,他吃素一年多,也不喝酒,然后性欲脆弱不堪了,他焦虑不安,他的女朋友也焦虑不安,陪着他去看了三个医生,前两个医生查不出病症所在,第三个医生问起他的食谱时,才知道是什么原因,告诉他多吃肉多喝酒就行了。他不再吃素,大口吃肉,大杯喝酒,性欲立刻强壮无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