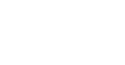转载:我们学校在盐城亭湖老城区
盐城市区就两个,亭湖区和盐都区。我们学校在亭湖区,是老城区,和盐都比,脏乱差。出了校门打车到市中心只要起步价,八块钱,有时候在市中心吃完晚饭,走着就回来了,大概要走一个小时二十分钟,不算远,也不算近。有一次从市中心的金鹰出来回学校,打不到出租车,我和两个朋友就搭了一辆小三轮。小三轮很黑,要我们十五块钱。那天晚上冷的一逼,我们就准备凑合一下,忍忍就到了。
开小三轮的是个老头,皮肤很黑,小三轮里本来就黑,这样我们就看不见他的脸了,只能看见几颗大白牙。小三轮里走人行道,有时候人行道很难走,他就会上机动车道。这样一来我就更提心吊胆了,我们的小三轮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,周围全是狼,恶的一逼。这个时候我安慰自己,小三轮比出租车视野好,可以观光。周围全是光,我们就四处看啊看,农村人进城,看见什么都新鲜。到学校要经过一个大桥,叫通榆河大桥。小三轮动力不行,没劲,上桥的时候慢的一逼,隐约还能闻见烧焦的橡胶味。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命悬一线,下面就是通榆河,我要是死了,明天应该能上盐城头条。还好我平时做的坏事不算多,我们顺利的过了桥。过了桥就到学校了。下车的那一刻,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坐三个轮子的车了。
每次从火车站出来,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有多么混乱。门口接客的车挤在一起,出租车黑车各一半,起亚,起亚,起亚,不管什么车都是起亚。火车站到学校也是起步价,但是司机都要把车厢塞满四个人才走,一人十块钱,个别司机还会要十五或者二十。嫌贵你就别坐,反正公交车你更挤不上去,一副爱坐不坐的小人嘴脸。这个时候我就想把司机杀了,尸体拿去喂狗。我只是这么想想,但是新校区的一个哥们真的这么做了,带着一股杀死比尔的怒气和司机干了起来,一死两伤。那一天火车站阳光灿烂,一群北方来的秃鹫盘旋着准备吃尸体,周围的人不自觉的唱起了祷告曲,气氛庄重而又肃穆。我很崇拜那哥们。
盐城风大,是真的很大。为了纪念盐城的大风,先人们在沿海的那一大片地上画了个圈,起名叫大风。后人觉得大风这个名字不够雅致,不好听,又改成了大丰。寒冬腊月的时候,宿舍楼道里经常听见风把玻璃吹碎一地的声音,男人的女人的尖叫声在楼道里回响,久久不散。晴朗的日子里风也大,女生宿舍晒的衣服经常满天飞,男人们就在下面追,一边跑一边淫荡的笑,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的味道。
上海人把长江以北的江苏人叫“刚波宁”,江北人,瞧不起。“书寓、长三、幺二、台基”,清朝的时候上海就把妓女分成三六九等,地位依次降低。书寓是最高级的那种,只能是上海人。下一等基本都是苏州无锡过去讨生意的,起码有个等级。苏北过去的则叫野鸡,全是逃荒躲避战乱过去讨生活的。盐城不喜欢被人当做苏北,但是也挤不进去苏南的圈子,常常以苏中自居,怡然自得。江苏的内讧这么严重,在某种程度上,上海功不可没。可我是苏北人我骄傲啊。
天快黑了的时候我路过操场,总会看见一对对情侣纠缠在一起,交换口水和唾液,各种体位都有。我路过他们的时候动静都很大,以此来表达我的抗议。有一次看见一个女的长得还很好看,在我的世界观里长得好看的女的是不能干这种事的。我于是走到他俩跟前儿,拉开他们纠缠在一起的肉体,一脸猥琐笑着对那男的说:“哥们让一让吧,该我了”。我于是就被揍了。被揍的那一刻我很开心,心里大喊真爱万岁柏拉图万岁弗洛伊德万岁萨特万岁加缪万岁,统统都万岁。
我擦干眼泪擦掉身上的血迹去隔壁的美食街找饭吃。美食街和我们学校只有一墙之隔,不知道什么人在墙两边都放了梯子,翻墙就成了很容易的事情,连没有腿的学长也能翻过去。美食街的全名叫富康美食街,流传在学生口中的是另外一个名字,叫堕落街。同学们这里不能来啊,来了你就堕落了。不能翻墙啊,翻墙你就堕落了。不能吃饭啊,吃饭你就堕落了。不能喝酒啊,喝酒你就堕落了。翻过墙看到的第一家店是一家自动贩卖成人用品的小店,店里的灯光是是粉红色的,这是荷尔蒙的颜色。我经常看到有少年在门口徘徊着进去了,他们宿舍肯定是又想换个女朋友了。
美食街的烧烤店老板总会烤完串就去后面打麻将,还老输,输钱了会用盐城话骂人,一脸沮丧就像刚吃完屎一样难受。卖炒饭的中年男人嘴里总是叼着一根烟,一边抽一边炒饭,油味和烟味混杂在一起,弥漫在路上。烟灰掉到锅里也没事,反正吃不死人,可能是烟灰炒饭比较好吃吧,他家生意一直不错。我也爱去他家吃炒饭,或者点一碗鸭血粉丝加一百多块钱的鸭肝,吃到哭。哭了就用店里的纸擦眼泪,纸不要钱,很划算。奶茶店的老板脸上总是笑眯眯的,逢人就说他下个月就要当爹了,他家奶茶很好喝。炸鸡腿的老板是个老烟枪,也是个猥琐的胖子,经常调戏他的女学生兼职,他店里的女学生经常换人,看起来他生活的很滋润。
学校看门的老大爷总是戴着老花镜看武侠小说,年轻的时候大概也是个狠角色。“你过去吧,我不拦你。”他总是对我这么说,“去学习吧,去奋斗吧,别和老师干架,别学我”。我心里一阵酸楚,嗯了一声就走了。
我们学校离机场很近,每天都有看起来超级大的飞机飞过我头顶,感觉一伸手就能把它打下来。我常常幻想,飞机快砸到我们学校里吧,结束这没有意义的一切。可惜到现在也没有飞机落下来,我很丧。
我突然从宿舍板凳上坐起来,踢开门要走。
“你们活着吧,我走了。”
“你要去哪?”
“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。”
“卧槽你到底要去干什么??”
“上厕所。”
文/周晓迪先生(简书作者)
原文链接:http://www.jianshu.com/p/c636eac57751
著作权归作者所有,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,并标注“简书作者”。